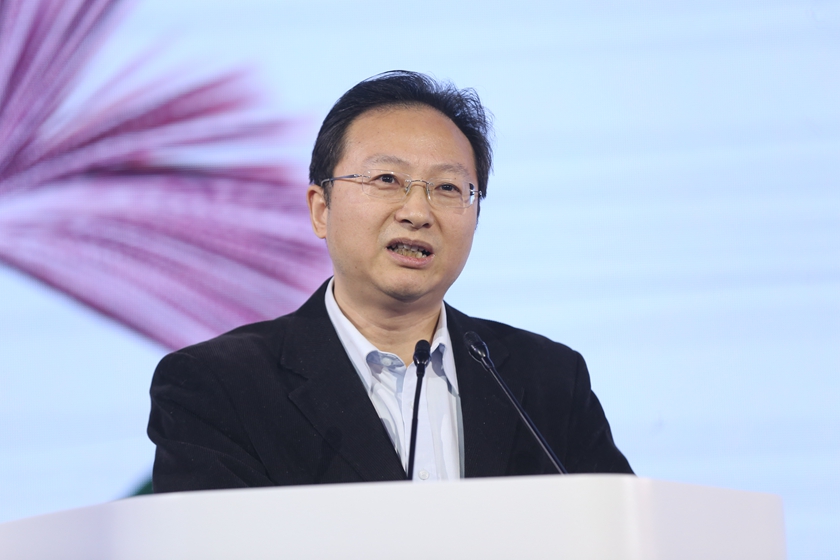友人来电知会元化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正在希腊出差。
先生离我们去了。
第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在上海衡山宾馆他的寓所。经友人介绍,我拿着自己的一篇文字登门向先生请教。先生看了,说喜欢我写的文字,要推荐给友人。我自感惭愧,因为带去的文字仅仅是对几个政治学概念的初浅的梳理。先生却高兴,说现在的很多学人不认真做学问,不深入研究前人的学说,不对已有的理论和实践作认真的梳理,而是直接提出口号式的、空洞的观点或主张。先生以为本人之拙作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并鼓励我继续深入研究。谈得投机,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告辞前,先生送我两本书,一本是《文心雕龙讲疏》,另一本是《思辩随笔》。那一年,先生已届杖朝之年。
我开始读先生的书,很喜欢,尤其喜欢几个月后先生托人带来的《九十年代反思录》。先生思维之敏锐,治学之严谨,反思之勇敢,让我由衷敬佩。其中,先生对“五四”的反思,与我以前一些零零散散的疑问和思考向碰撞,我的眼睛一亮。
因身在异地,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基本每年拜访先生一次。第二次见到先生,是首次见面一年以后。我们谈到了“五四”。先生说自己对“五四”的反思是很痛苦的,因为先生一直认为自己是“五四”的儿子。痛如斯,先生没有回避,因为先生的苦难经历和知识分子的品格不允许先生逃避。我说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在思考“五四”时期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为什么“权利”等字眼在当时不提或提得不够。读了先生对“五四”的反思,我找到了一些原因。我还说,先生对“五四”时期流行的意图伦理的批评,与美国建国之初联邦党人对反联邦党人的批评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汉密尔顿写到:“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念,而且直率地向你们陈述这些信念所根据的理由。意图之善良不允许含糊其辞的表述,但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听到汉密尔顿对意图伦理的警惕,先生表示赞赏。
先生学贯中西,对西方思想史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对中国的近代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人物,先生有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有一年见面,我们谈到卢梭。先生说“五四”宣扬“德先生”,却没有对有关“德先生”的理论和实践作全面深入的研究。“五四”时期的学人受卢梭的影响很大,却不知道卢梭的学说只是一家之言,对卢梭本人的思想也缺乏认真的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生曾对卢梭的思想进行过认真的梳理,进一步认识到卢梭的公意论与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先生要我说说意见。我说关于先生对卢梭的研究,尤其是先生关于卢梭对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影响的研究,我表示赞同,尤其钦佩先生对卢梭著作的认真细致的研读和考证。但有一点,我提出希望先生注意,那就是卢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学说也很复杂,持截然不同观点的人常常都可以从卢梭的著作中找到一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述。卢梭的国家学说和公意论容易导致专制,但也可以从他的公意论中推导出法治以及法治框架下的民主。事实上,卢梭的本意应该不是专制的,只是很多后人把他的部分思想同一些激进的政治主张相结合,形成激进主义的思潮和实践。换句话说,卢梭的国家学说容易被激进主义所利用。先生仔细听了我对卢梭公意论的另一种解读,说这值得研究,要我把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写出来。先生就是这样,不摆驾子,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总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讨论问题。
又有一年,我们见面谈认识论。先生问,有绝对的真理吗?也许有,但是人能够完全地掌握绝对真理吗?先生说,作为一个受启蒙思想影响很深的人,先生曾经对人的理性充满信心。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经过多次艰苦的研究和反思,先生开始看到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先生认为,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很重要,否则就会神化人的能力,就可能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去压制异己,走向专制。我以为先生的体会与很多启蒙思想家是一致的。我说,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都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人性的两个特点,即自利倾向和有限理性。启蒙思想家们天然地怀疑自诩的高尚或绝对的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卑微无望的。相反,摆脱了“绝对真理”的束缚,人们才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先生说,可惜到了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我说不晚,先生一生的追求,对“理性”一词作了最深刻的诠释。
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比起来,在新世纪中先生更加忧虑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尤其担忧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膨胀。有一年见面,先生说,市场经济鼓励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但应该有限度。西方人在俗世生活中追求功利和物质,但他们同时还有宗教生活,通过宗教生活实现对功利和物质的部分超越,从宗教生活中吸取精神的资源。而在当前我们的社会中,很多人没有超越的领域,他们沉溺于功利或物质不能自拔,把理性完全当作实现功利或物欲的工具,急功近利,缺乏敬业精神。要改变这一现状,先生认为,需要多方努力,但知识分子尤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应该警惕学术上的功利主义。我说,先生所关心的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问题具有普遍性,不仅中国面临这样的问题,很多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当然,由于我国特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先生指出的有些问题在我国比较严重,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不努力加以改变,可能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方向和效果。因此,我非常同意先生对道德文化和精神生活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担忧。
不到两年前,先生的夫人逝世。我登门拜访,希望能安慰先生。我从没有见过先生的夫人,但早就听说张可女士的善良和聪慧。同上一次见面相比,先生明显老了许多。先生是一条硬汉子,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到七十年代末,先生历经苦难,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都没有把先生打垮。但提起张可女士,先生的眼睛里透出一种温柔的感情,他是如此深爱着夫人,夫人的善良和贤惠陪伴先生走过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夫人离他而去,先生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看着先生忧伤的眼神,我试图说一些安慰的话,却发现自己口齿之笨拙。纳兰性德有词云:“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沉思往事立残阳。”先生此时的痛苦,有谁能够真正体会呢?
后面几年,先生已经不能提笔写作,只能靠口述。先生很着急,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去年见面,我们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先生对传统文化面临的衰落深表担忧。先生说,按照梁启超的划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可以区分“根本精神”和“派生条件”的,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应该也可以继承的。这种继承,先生说,不是复古,而是应该与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治理念相结合,有所发展。这种继承应该是往高处走的。正如杜亚泉引孟子所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通过这种继承,先生试图推动东西文化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我说,近年来有一些对先生的误解,以为先生关心道德和传统问题是要复古,要倒退。其实严肃的学人都应该认识到,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人文精神,正如先生自己所说,“倘深一层去看,我所关怀的是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我接着说,先生的思想和杜维明先生的新儒学都强调了继承传统文化的可欲性和可能性,但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总结传统文化,二是如何区分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与派生条件,三是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根本精神是不是可以独立于派生条件而得到继承,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价值相结合等等。先生点点头,说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来。
听友人说,先生病危期间还问起我,我的眼圈红了,后悔忙碌于琐碎杂事,没有在先生病危期间赶去探望,没想到去年一面竟成永诀。回想起来,我有幸与先生的诸多朋友和学生一起,陪先生走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尽管见面不多,我们的精神是一直相伴的。我所了解的,只是先生的一个侧面,但我从这一侧面中看到了森林,看到了海洋,看到了不屈不挠的理性良知和批判精神。从探索黑格尔的普遍规律到关注个体的特殊的经验,从相信人的理性无坚不摧到“我知我之不知”,从无条件接受“五四”的遗产到批判性继承“五四”精神,从推动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到对商业和科技文明的后现代反思,先生心怀人文,心怀社会,一路探求真理,从未放弃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如今先生去了,对于我们青年人来说,以先生为榜样,以人文关怀和理性良知为基石,继续先生未竟的事业,是作为后人起码的责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雅典,我站在苏格拉底的塑像前。苏格拉底与元化先生,上下两千四百年,历史是不是有相似之处?我想起王安石的一首诗,先生曾借此诗来表达对顾准先生的怀念,在此用来怀念先生,也是很恰当的:“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廖。”
2008年5月